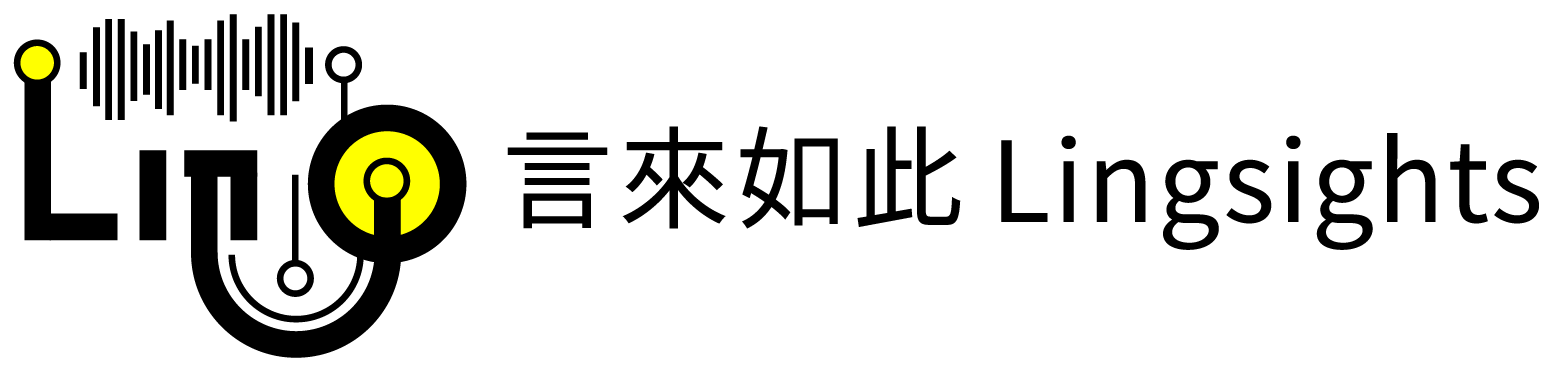語言不只是溝通:從尼加拉瓜手語看人類心智的創造本質
你覺得語言的本質是什麼?還記得在語言學概論的第一堂課,討論這個問題時,許多人(包括我)都覺得:「語言是溝通的工具」。巨觀來看,語言確實是溝通的橋樑,但這篇文章將透過尼加拉瓜手語誕生的歷程,揭示人類發展出語言的能力或許不是為了溝通,而是為了創造更多組合。而這樣的發現,也許能引出更深一層的思考:若語言天生傾向於創造,那麼人類的本質,會不會也是?

文:黃綵誼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語言是什麼?
自從我們誕生到這個世界,語言能力就悄悄在我們的腦袋中發展茁壯。當我們在約莫 12 個月大時吐出第一個單詞,便像打開了一道閘門,之後以驚人的速度學會各種抽象的詞彙與語法,在 2 歲左右,小孩平均每天能學會 8 至 10 個新詞,6 歲時便能掌握超過 1 萬個詞彙,並可以自然運用複雜的語法結構,這是其他物種,甚至人工智慧無法企及的。人類究竟有什麼樣的內建機制驅動著我們學習語言?發展出語言能力是為了什麼?是溝通、理解嗎?
若要理解語言的本質,或許我們可以從釐清語言與非語言的差異來切入,而手語和手勢的差別正好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手語和手勢有什麼不一樣?
手語並不只是手勢,而是一個完整的語言。
美國手語(ASL)、台灣手語(TSL)、日本手語(JSL)等,都被列為世界語言之一,是各自獨立的語言系統。它們有著穩定的文法、母語者,以及人類語言獨有的關鍵特性:離散性(discreteness)、無限性(productivity)與遞歸性(recursivity)。從神經科學的研究來看,與語言處理相關的左腦(特別是左額下回與左上顳回)在使用手語與口語時皆會強烈活化,顯示手語與口語共享語言處理的神經基礎。
那什麼是離散性、無限性與遞歸性呢?用一句話來說的話,就是語言能夠「用有限的符號,創造無限的組合」。
舉例來說,在比「手勢」的時候,表達會比較直觀連續。想傳達「球往右邊滾」,我們會用手模擬球的形狀,同時讓它在空中翻滾移動,語意是整體輸出的,較難靈活組合。但在「手語」中,我們會把這句話拆成三個獨立的單位:「球」、「滾動」、「往右」。這種解構雖然會讓表達與理解的過程更費時費力,卻賦予語言極大的彈性與創造力,也讓人類可以表達出幾乎無限的思想與情境。
而接下來我們會看到,這種「把連續動作拆解為離散單位」的傾向,竟然會在周遭沒有其他手語或口語語言刺激,接收到的輸入幾乎都是連續手勢的聾人兒童身上自發產生,成為尼加拉瓜手語誕生的關鍵一步。這也暗示著我們人類的心智,或許有種天生的動力,將經驗「語言化」、抽象化,以利創造。
一個新語言的誕生:尼加拉瓜手語
在2004年發表的一篇語言學研究中,研究者觀察了尼加拉瓜聾人社群如何在幾乎沒有接觸現有語言系統的情況下,自發發展出一套手語。藉此,他們觀察,人類在缺乏語言輸入的環境中,是否仍會自動建構出語言的核心特質(離散性、無限性等),以及語言如何從非語言逐步演化而來。
背景:語言從無到有
1970 年代以前,尼加拉瓜的聾人社群彼此幾乎沒有互動。當時的社會環境對聾人不友善,大多數聾人長時間都待在家中,缺乏教育、醫療與社交資源,也很少與其他聾人建立穩定的關係。也因此,在那個時期尚未出現手語這樣的完整語言系統。
然而,即使沒有「語言」,人類為了想盡辦法表達自己、溝通、合作,聾人家庭中發展出所謂的 「家用手勢」(home signs),每個人或家庭為了彼此理解,自創的一套手勢系統。但這些系統彼此間有很大的差異,幾乎無法傳承或通用,語言性也相當有限。
關鍵轉捩點:學校與群體的形成
情況在 1977 年起出現快速的變化。當時尼加拉瓜開始設立聾人特殊教育小學,1981 年開設聾人職業學校。孩子們開始定期聚集在學校,多了課堂上與課外的持續交流。雖然學校的課程以西班牙語進行,聾人小孩們開始自行發展一套為了彼此交流而生的新手勢系統。
這套系統很迅速地從簡單的 home signs 演變成更穩定、可傳承的語言,尼加拉瓜手語(NSL, Nicaraguan Sign Language)。它的使用者數量快速增長,到了研究進行時(2000 年代初期),已有超過 800 名使用者,年齡從 4 歲至 45 歲不等。
特別的是,在尼加拉瓜手語中的發生的演化,無論是新的語法或新的表達形式,幾乎完全由「準青春期」的小孩主導,並往低年齡層擴散,由更年幼的孩子進一步學習、優化。成年人則大多保留早期版本,較少掌握後來發展出的語法特徵。
研究方法與觀察重點
研究團隊比對了三個世代的 NSL 使用者,最年長的第一代(1984 年以前出生)、第二代(1984–1993 年)、最年輕的第三代(1993 年之後),並以聽力正常的西班牙語母語者,說話時自然的輔助手勢,作為對照組。
研究引導參與者描述有「動作」與「路徑」的概念,例如「滾下山坡」、「爬上牆壁」等等。表達方式可分為兩類:
同時性(simultaneous): 同時比出動作與方向
次序性(sequential): 動作與方向分開比,有線性次序
從連續手勢到離散語言
結果發現,所有西班牙語者和七成以上(73%)第一代 NSL 使用者都傾向使用「同時性」表達方式。這代表他們的手語形式仍高度仰賴直觀的動作模擬。而到了第二、三代的使用者,僅有三到四成保留這種方式(32%、38%),其餘大多數都採用「次序性」的解構表達,也就是把「滾」和「向下」分開比。
圖:Children Creating Core Properties of Language: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Sign Language in Nicaragua
(A)同時表達方式與路徑。一位西班牙語使用者在描述一隻貓以搖晃、翻滾的方式快速地沿著陡峭的街道向下移動的情境。圖中顯示的手勢是自然地配合他語音出現的。在這裡,「方式」(如搖擺)和「路徑」(向說話者右方的移動軌跡)是以一個整體的動作同時表達的。(B)依序表達方式與路徑。一位第三代尼加拉瓜手語使用者描述相同的翻滾事件。在這裡,「方式」(如旋轉)和「路徑」(向手語者右方的移動軌跡)是以兩個獨立的手語符號分別表達,再組合成一個有順序的動作序列。
令人驚訝的是,從早期的手語動作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手語是源自於手勢,但第一代的孩子們卻自發地開始把原本連續的手勢拆解成「離散」的單位,這不是為了更方便理解,而是為了靈活性與創造性。將運動方式與路徑拆成不同單位後,不同的方式與不同的路徑可以相互搭配,創造出更多組合,例如可以表達「往上翻滾」、「往下旋轉」等等。這種解構與組合的傾向,不但延續到了後來的第二、三代,還進一步演化出穩定的語法模式。
語言演化的內建機制
這樣的現象不只出現在 NSL,即便在已成熟的語言中也能觀察到類似情況。像是在美國手語(ASL)中,雖然成人會同時比出多個意義單元組成的複雜動詞,但小孩在學習階段,依舊會自動傾向將這些結構拆開來分別學習、比出,再逐漸重構成複雜形式。
這些研究都顯示,即使環境中提供的是連續、直觀的訊息,也沒有溝通理解上的障礙,小孩的大腦也會主動「解構、分析、重組」這些訊號,來創造出更多、更靈活的表達方式。這或許告訴我們,比起「理解並複製」,「創造與建構」才是語言的本質,甚是人類的的本能。
人生來是為了創造
語言作為人類心智活動的縮影,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我們內在「創造」的本能。跳出語言系統的框架來看,在音樂、藝術、科學與技術等各個領域中,也不斷試圖拆解現象,將複雜轉化為離散的符號,去重組出無限的意義與可能。
哲學家維根斯坦曾說:「語言的邊界,即是思想的邊界,也就是世界的邊界。」如果語言只是為了表達,我們大可只使用簡單的圖畫、表情,但人類選擇了更複雜的方式,我們解構、抽象、分類、命名,正是為了突破理解的限制,去尋找更多的可能性,擴展思想與世界的邊界。
但在成長的過程中,這樣的創造力往往會逐漸消退(我也很好奇為什麼),有時是主動放棄,有時是被動遺忘,正如第一代 NSL 使用者,他們雖參與了語言的誕生,卻無法承接它的演化。我們每個人一定都曾經是個充滿創意與想像的小孩,能夠把積木堆成奇形怪狀、畫出不存在的動物、創造只有自己懂的語言,只是一路上漸漸被雕塑成「能夠模仿」而非「能夠創造」的人,我覺得這是件有點可惜的事。
創造的能力是寫在我們基因裡的,這樣的能力不應只存在於童年,即便到了前額葉近乎不再發展的這個年紀,我們可以也應該要繼續用各種媒材去創造,創造新的、屬於自己、也屬於這個世代的東西。
後記:從材料系跨域探索的心得
大家好,我是這篇文章的筆者,黃綵誼,陽明交通大學材料系的學生。材料系的來撰寫語言學科普文,著實有一點奇妙,但這是我大學三年探索的路上一段真實旅程。從高二開始當了五年的理工人,用數字去了解世界,但我漸漸覺得,我想了解的好像是「人」,於是開始對語言學、認知科學、心理學、甚至哲學產生興趣。
身在一個準工程師的科系,當身邊同學都在做專題的時候,我卻把時間和心力拿去修了許多藝術、音樂、多媒體等等很文組的課,其中也包括外文系的〈語言學概論〉和〈語言與人類心智〉。其實自己也很多次懷疑我只是在逃避那些困難的公式,害怕我這是把時間丟進水裡。不過回過頭來看,我在跨域的路上,遇見了很多很棒的老師,很有教學熱忱,也很願意鼓勵學生問問題、表達自己的想法,讓我重新找到了學習的快樂和熱情,很開心!
我覺得我之所以能有勇氣相信自己的選擇,走了一條不太典型的路,要感謝很多人的鼓勵,所以也想在最後藉由自己一點點的心得分享,給那些正站在迷惘路口的大家一些參考和勇氣。
參考資料
Ann Senghas et al. ,Children Creating Core Properties of Language: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Sign Language in Nicaragua. (Science 305, 1779-1782(2004). DOI: 10.1126/science.1100199)
Emmorey K (2021)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Neurobiology of Sign Languages. (Front. Commun. 6:748430. doi: 10.3389/fcomm.2021.748430)
文章分類
標籤
作者介紹

特約作者
由我們邀請擔任特約作者的語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