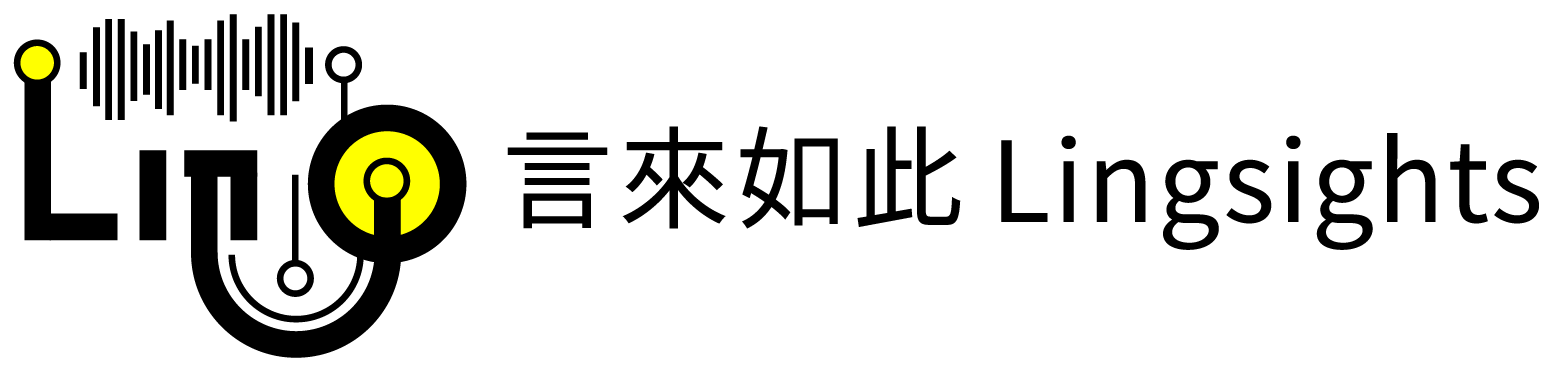語言如何映照身份—Hall-Lew與Starr的社會語音學對話(下)
你是否曾以為,語言變異就是「說話有口音」?又或者以為語言風格就像換衣服一樣,今天講台灣國語、明天模仿LA Valley Girl?事實上,語言的差異遠比我們想像得複雜,也比我們以為的更難「設計」與「控制」。

文:花湧惠
延續上篇專訪,我們繼續與來自英國與新加坡的兩位語言學家——Lauren Hall-Lew 與 Rebecca Starr 教授——聊聊那些語言學常見迷思、語言學研究的未來與進修建議。如果你還沒讀過上篇,歡迎點擊〈語言如何映照身份—Hall-Lew與Starr的社會語音學對話(上)〉先行閱讀。
不要再誤會啦!語言使用真的不是刻意的!
你是否曾以為,語言變異就是「說話有口音」?又或者以為語言風格就像換衣服一樣,今天講台灣國語、明天模仿LA Valley Girl?事實上,語言的差異遠比我們想像得複雜,也比我們以為的更難「設計」與「控制」。
Starr首先提醒我們,語言變異不只發生在聲音層面,還涵蓋語法結構、語助詞、語意強度詞等不同維度。聲音變異的研究之所以特別多,除了因為語音訊號在自然語料中更容易被偵測之外,Starr更指出,這還與英語本身的語音系統有關:「為什麼那麼多變異研究聚焦在聲音上?因為英語的語音變異真的很多,特別是母音,整體上是個特別豐富的聲音系統。(Why you get a lot of sound-based work is because English has a lot of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nd it has a kind of unusually rich vowel system.)」加上英語在語言學研究中的主導地位,導致研究焦點往往傾向語音變異,也因此讓人誤以為「語言變異就是聲音變異」。
Hall-Lew 則指出一個更容易被誤解的面向:「語言風格」(Style)。他觀察到,許多學生,甚至語言學者,常誤以為語言風格是一種可以自由切換的表演,例如政治人物在選舉演說中會刻意拉高聲音、放慢語速,似乎是在「扮演」某種身分。但在第三波社會語言學(Third Wave Sociolinguistics)的理論中,風格建構(style construction)往往是潛意識的自然流露,而非明確的策略選擇。Hall-Lew 解釋:「大家以為建構語言風格就像穿上一件特定風格的外套,但我們的意思是,說話者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在這個世界裡生活,而語言就是他們自然的一部分。(They think we mean like putting on a certain style of jacket, but we just mean they're being who they are in the world, and part of that is language.)」Starr 也補充說明:「在論文中我們常用『draw on』來形容說話者使用特定語言特徵,但這不代表他們是有意識地做出這些選擇。 (We say a speaker “draws on” different variables to construct a persona… but that doesn’t mean it’s intentional.)」
在「第三波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下,語言風格並非刻意模仿,「我們是誰」與「我們如何說話」會彼此牽動、相互形塑,即語言與身份是交互建構的關係。因此,將語言風格誤認為是一場刻意的模仿秀,正是我們對語言最常見、也最該被打破的迷思之一。
那些還沒開發的寶藏—語言學界的潛力研究
語言學,不只是語法與發音的學問,更是一種觀看人類社會的方式。那麼,當代社會語言學者眼中最值得關注的議題是什麼?
Starr 提出,他最關心的議題之一是「語言變異的認知處理」,也就是人類大腦如何理解、儲存、運用語言中的變異。他以英語中的/t/和/d/省略現象(TD deletion)為例說明,當一個母語者聽到像 “west” 或 “cold” 的詞尾子音被省略,即使換作從未聽過的新詞,他們也能自然地「套用」這項變異規則。這顯示語言變異不只是統計數字,更深植於我們的感知機制中。
Starr 舉出社會語言學之父 William Labov 在2005年的「(ING)」變異研究,說明大腦如何處理語言的出現頻率。只要新聞主播在播報中用了一次 “runnin’” 而非標準的“running”,觀眾就會覺得他不夠專業。這顯示,語音變異的社會評價並非線性計算,而是對「稀有語音」特別敏感,人腦會放大這些少見變體的社會意義。
Starr 眼睛一亮地接著說:「我們的大腦到底是怎麼做到的?是透過一條明確的規則?還是認知上的限制?(Do we have a rule in our brain? Do we have constraints in our brain? What’s happening?)」他認為,這些現象背後牽涉的,是語言學與神經科學的跨領域研究,而在科技發達的現代,學者們更可以透過腦波儀(EEG)等技術來觀察大腦面對語言變異時的即時反應。這類跨學科研究,有望帶來對語音感知、語言偏見與社會認同之間關係的全新理解。
除了認同神經科學與語言學的跨領域發展潛力,Hall-Lew 也從語言學的語言類型多樣性(typology diversity)角度切入。他身為《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主編之一,正在積極推動語言學研究納入更廣泛的語言樣本。他直言:「除了英語以外,幾乎所有語言在社會語言學中都是『被忽略的語言』。(Understudied languages are pretty much every language besides English.)」Hall-Lew 舉了觸覺手語(tactile sign languages)作為例子。觸覺手語是一種在聾盲社群中透過觸碰進行溝通的語言形式,由於其語言機制不依賴視覺或聽覺,幾乎未被納入主流社會語音變異的研究之中。
Hall-Lew 呼籲語言學界應更重視這些弱勢語言的觀點。畢竟,若我們僅以英語、或可聽見、可看見的語言為基準來建構理論,那我們對「語音變異」的理解,很可能只會停留在冰山一角。
語言學的全球視角—給臺灣學生的求學建議
語言學作為相對冷門的學科,對許多臺灣的學生來說,「該去哪裡學語言學?又該從哪裡開始準備?」是個很大的煩惱。而兩位教授也針對臺灣學生提供了豐富的參考建議。Starr 指出,新加坡的語言學研究與美國不同。當地的語言標準並非單一,而是多元並存,有新加坡式英語(Singapore English)、英式英語(British English)、美式英語(American English),以及強調在地文化脈絡的「世界英語(World Englishes)」理論。Starr表示,這些是自己於美國學習語言學時沒有學過的概念,卻是新加坡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針對新加坡英語的理論,許多都只適用於新加坡當地,沒有被在其他地方被應用。因此,研究者必須學會與這些在地理論對話。(For how Singapore English works, that have not been applied to any other region of the world, so you have to engage with that literature as well.)」
他更提到在執行研究時會遇到的實際挑戰。由於大學生的社交圈通常只涵蓋和自己背景相似的人,要找到來自工人階級或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參與者並不容易。這意味著,若要蒐集更多元的語料,就得走出校園、走進社區。「在大學體制中,要蒐集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語料非常困難。(In a university context, it's really challenging to collect data from a wide range of social classes.)」這樣的困境,也揭示語言學在不同社會結構下的實踐限制與可能盲點。
Hall-Lew 教授則分享他在美英兩地研究社會語言學的觀察。雖然理論源流相通,但研究重點有著微妙差異。美國的社會語言學較常以「種族」為研究變項,英國則更聚焦於「階級」。他補充,英國與美國的語言學界也有各自獨立發展的學術傳統,美國學者多引用美國學者,英國學者則多引用本地文獻,這樣的知識體系區隔,導致雙方可能做出相似的發現,卻彼此不知對方的存在。
「我發現,把這兩個知識脈絡放在一起觀察,是件很有趣的事。有時他們說的是同一件事,卻不知道彼此的研究。(I found it interesting to kind of blend the two and see where one is saying the same thing as the other, but they don’t know about each other.) 」Hall-Lew 說。他更提醒學生,若計畫前往英國攻讀博士,通常需要在申請時就提出明確的研究計畫,這與美國「邊修課邊探索」的博士訓練方式截然不同。
那麼,臺灣學生該如何開始準備呢?Starr強調,博士研究最重要的並非先備知識,而是「研究能力」。能提出問題、主動參與專案、學習工具(如 Python 程式語言),都能展現出研究潛力。「我們不希望學生只是說:『教授您給我什麼題目,我就做什麼。』(We don’t want students who say,‘I’ll just work on whatever you want me to work on.)」Starr 笑說。除此之外,他也推薦對語言學感興趣但尚未確定研究方向的學生,先考慮去新加坡攻讀「課程型碩士(coursework master)」,如此一來,可以先累積學術基礎與研究經驗後,再申請歐美博士班。新加坡的語言學學術環境完整,對華語使用者也十分友善。
從風格的迷思、認知的理解到語言多樣性的思考,我們在這次的專訪中,看見語言學如何映照出我們是誰,也塑造著我們能是誰。語言從來就不只是溝通的工具,更是日常生活中一再協商、調整、體現身份的痕跡。
文章分類
標籤
作者介紹

陽明交通大學外國語文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向以理工、醫學及管理見長,有鑒於科技的發展宜導以人文的關懷、博雅的精神,而資訊的流通則取決於語文的運用,因此於民國八十三年八月成立外國語文學系。
本系發展著重人文與科技之深層多元整合,以本系文學、語言學之厚實知識素養為底,再廣納本校資訊理工、管理、醫學以及其他人社領域等豐厚資源,創造多元與融合的學術環境,開拓具前瞻性及整合性之研究與學習,以培養兼具系統性思考及人本軟實力的學生,使其成為兼具在地及國際性多層次觀點與分析批判能力的未來領導者。
在研究所的規劃上,語言學方面主要是結合理論與實踐,特別重視學生在基本語言分析及獨立思考能力上的訓練。除語言各層面的結構研究外,本系也尋求在跨領域如計算機與語言的結合及語言介面上之研究 (如句法語意介面研究)能有所突破,並以台灣的語言出發,呈現出台灣語言(台灣閩南語、台灣華語、南島語)多樣性,融入社會觀察,如自閉語者聲學、聽障相關研究、社會語音學研究以及台灣語言的音變等。
相關文章

為什麼有些語言像在「唱歌」?聲調語言的分布、演化與生態之謎
為什麼世界上有些語言有精細的聲調系統,而有些語言(如英文、德文)卻相對平坦?有研究發現,這樣的區別不只是偶然,其實是與我們的喉嚨構造、環境氣候,甚至是基因遺傳有關。

語言不只是溝通:從尼加拉瓜手語看人類心智的創造本質(台灣手語翻譯版)
你覺得語言的本質是什麼?還記得在語言學概論的第一堂課,討論這個問題時,許多人(包括我)都覺得:「語言是溝通的工具」。巨觀來看,語言確實是溝通的橋樑,但這篇文章將透過尼加拉瓜手語誕生的歷程,揭示人類發展出語言的能力或許不是為了溝通,而是為了創造更多組合。而這樣的發現,也許能引出更深一層的思考:若語言天生傾向於創造,那麼人類的本質,會不會也是?